这本女版的《活着》,不比余华写得差
说起余华的《活着》,我相信很多人都被福贵的人生经历打动过。可我一直在想,还有没有像《活着》这样好看的小说呢?
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有人推荐韩国作家 崔恩荣的《明亮的夜晚》,说这本书是女性版的《活着》
我当时心想,真有这么厉害吗?于是抱着好奇的心态下单买来读,没想到写得非常好,说得夸张一点真不比余华写得差。
这本《明亮的夜晚》讲述了四代韩国女性的故事。主人公「我」在离婚后来到海边小城熙岭,偶遇多年未见的祖母。
通过祖母的讲述,「我」了解到了曾祖母、祖母、母亲以及自己的人生经历。故事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一直延续到现代,跨越了近百年的时间。
书中的女性角色们都经历了许多苦难。曾祖母出身白丁(朝鲜时代的贱民阶级),为了逃避被日军抓去当慰安妇的命运,嫁给了一个自以为是她救世主的男人,却遭受了无尽的羞辱和虐待。
祖母被父亲随意许配给一个已婚男人,丈夫重婚后抛弃了她和孩子。母亲为了逃避家庭的阴影,远走他乡,却在婚姻中重蹈覆辙。而「我」也经历了婚姻的失败。
这些女性的故事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在中国家庭里,我们也能听到类似的遭遇。可是崔恩荣并没有把这本书写成一部悲情小说,相反,她让这些女性角色在苦难中互相支持,彼此取暖,展现出坚韧不屈的生命力。
那不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的夜,而是充满隐隐光辉的明亮的夜。 」女性人物之间的互助互爱,支撑着彼此,走过了人生里的一程又一程。在这无尽的黑夜中,因为有了光这一切才有可能。
这句话也是本书的主题。在那个男权社会里,女性们虽遭受着各种不公平的对待, 但她们并没有被命运打倒,而是通过互相扶持,在黑暗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光明。这种女性之间的友谊和力量,才是整本书最动人的地方。
那为什么说这本书是女性版的《活着》呢?
一是这两本书都是讲述普通人在大时代背景下的生存状态 。《活着》中的福贵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而《明亮的夜晚》中的女性角色们则经历了日本殖民统治、朝鲜战争等历史变迁。
二是这两本书都让读者看到了人性的坚韧 。福贵在一次次的打击中顽强地活着,而《明亮的夜晚》中的女性们则在父权社会的压迫下坚强地生存下去。她们都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什么叫「活着」。
不过,《明亮的夜晚》比《活着》多了一层温暖。在福贵的故事里,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个人的挣扎,而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了女性之间互帮互助的力量。这种力量让整个故事多了一丝希望和温情。
再说说这本书的语言。崔恩荣的文字非常细腻,她能把人物的情感刻画得入木三分。
比如写曾祖母和新雨大婶之间的友情时,她写道: 「新雨啊……如果我死了,肯定见不到阿妈,也见不到你。因为我们会去不同的世界。我绝对去不了新雨你所在的地方。」 这样的文字,让人读了忍不住鼻子一酸
还有一点让我觉得这本书很棒,就是它不仅仅局限于讲述悲惨的故事,而是通过这些故事反映了社会问题。比如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家庭关系的代际传递等。这些问题在今天看来依然很有现实意义。
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好像看了一部跨越百年的韩国女性史。它让我对韩国女性的生存状态有了更深的了解,也让我对女性之间的友谊有了不一样的认识。
如果你喜欢《活着》,我觉得你一定喜欢这本《明亮的夜晚》。读完了这本书,我想你感受到的不是《活着》里的无奈,而是 在最黑暗的时刻,你也能看到希望的光亮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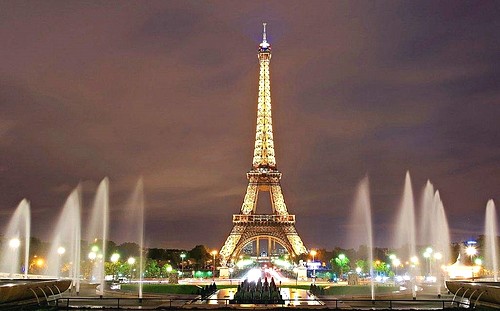
余华:人生就是几步而已
在北京,张晓刚的工作室与我的住处隔了一条宽阔的马路,我在窗口可以看到他工作室的屋顶,在他工作室的窗口也可以清楚看到我住的公寓大楼。我们的视野里知道对方在那里,但是不知道具体在哪里。我们交往密切,相谈甚欢,但是有些话题不会触及,因为生活里不是所有的门都会打开。
在他的艺术生涯里为我们诚恳地打开了一扇扇作品之门。
从他川美的毕业作品《草原组画》(1981)开始,此后的几年里他像个摊贩那样为我们铺开了一个个作品系列。1994年,《血缘:大家庭》系列来了,他的命运因此出现了重大转折。他不再像个摊贩,终于像个艺术家那样到处受人尊敬,之前只能在少数几个朋友的脏话里感受到的尊敬很快普及开来了。
张晓刚的艺术生涯里没有出现过跳远的步伐,他走得不快,可是他的步伐很大,毕业作品《草原组画》就是这样,他一步跨出了当时流行的写实主义和伤痕美术。也许是草原的辽阔让他的画笔和调色板也辽阔起来,组画的线条是粗壮的,色彩是粗壮的,动物人物是粗壮的,即使神态也是粗壮的。这九幅组画在41年后的今天再来欣赏,让我感到自己的心情顷刻间也粗壮了。十几天前我见到一位20年前在云南迪庆见过的藏族朋友,我觉得他瘦了很多,他说没有瘦,他说当时穿着藏袍。我脑子里马上出现了张晓刚的《草原组画》,生活就是粗壮的,精细是选择出来的,或者说生活在不同的环境时所呈现出来的也不一样。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大学毕业生是社会上的香饽饽,可是有着大学生名头的张晓刚不仅没有找到想要的工作,就是不想要的工作也没有找到。张晓刚在等待时期去玻璃制镜厂做了临时工,去干最脏最累的活,每天有两元收入。他年纪不小了,不能再让家里养着自己。之后有了朋友的推荐,还有 》杂志的封二发表了他《草原组画》里的《暴雨将至》,他终于有了正式工作,一个舞台美工,同时又要拉大幕还要管理服装。由于他工作出色,经常借调出去,他的创作时间越来越少。他完全可以吊儿郎当,这样会迅速减少单位工作量和借调出去的次数,从而增加自己的创作时间。可是他做不到,他是一个做什么都认真的人。之后机会出现了, 开设师范专业,需要增加老师,张晓刚借调到了川美,成为一名代课老师。他如愿留了下来,正式调入了川美。
他没有停下来,继续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去,留下了《遗梦集》《重复的空间》《手记》。
张晓刚的毕业创作《草原组画:天上的云》
这个时期,张晓刚和我的故事开始了。我们两个,一个画家和一个作家第一次重合出现了。当时我们各干各的,相互之间不认识,可是我们的作品是精神上的邻居,远亲不如近邻的邻居。1984年,“幽灵”出现在了他的《住院日记》里,1988年,“幽灵”来到了我的《世事如烟》里。之后张晓刚“遗梦”里的想入非非,“重复的空间”里的冷酷,“手记”里的暴力,也是我1986年到1990年梦魇般的创作旅程,现在来看,我们两人在那个时期的有些作品可以互相命名,比如他的《除夕夜》可以命名我的《现实一种》,我的《往事与刑罚》可以命名他的《手记3号:致不为人知的历史作家》。
1993年开始画《全家福》时,张晓刚说:“我用了大约一个多月反复去画一张肖像,同时每天反复地去‘看’那些老照片。逐渐地,我开始有了一些认识。”他被那些家庭旧照片触动了,虽然他不知道哪里被触动,只要他感受到有触动就足够了。
1994年《血缘:大家庭》系列开始,他走出了暗道,走上了张晓刚之路。我能够理解从《全家福》进入到《大家庭》的社会学和历史学意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和工作的经历。那个时候单位是一个大家庭,社会也是一个大家庭。张晓刚结束欧洲之行回到川美这个大家庭,从个人主义回到集体主义,因此,张晓刚在创作《血缘:大家庭》系列时,取消了个人的人,画下了集体的人。
张晓刚在画室里完成一幅又一幅这个系列的作品时,已经译成英文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正在美国的出版社那里碰壁,一位美国编辑写信问我:为什么你作品中的人物只是承担家庭的责任,不去承担社会的责任?这位美国编辑不知道,在中国3000年的国家历史里,个人在社会中是没有位置的,所以在家庭中的位置才会如此重要。也因为如此,中国的社会纽带不是个人和个人连接的,是家庭和家庭连接的。需要说明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个人主义兴起之后,这才开始有了变化。
我们两人重合的故事还在继续。当张晓刚在画布上全神贯注展现单纯的力量时,《马太受难曲》的影响让我尝试用短篇小说的方式去写长篇小说,我写下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张晓刚在1993年之前有着表现主义的标签,其实他也弄不清楚自己是表现主义,还是超现实主义,总之他是一个现代派。我在1992年之前是先锋派,我也弄不清楚先锋派的定义是什么,我80年代写下的小说冷酷又暴力,文学评论家称之为“零度写作”,张晓刚那时期的《重复的空间》系列和《手记》系列也是冷酷又暴力,也许可以称之为“零度绘画”。1993年《全家福》之后的张晓刚,尤其是1994年进化成《血缘:大家庭》之后的张晓刚,让一些美术评论家满脸疑惑,那个表现主义的张晓刚去哪里了?他因此遭受了不少批评,与我当时《活着》出版后遭受的批评几乎一样,起因是那个先锋派
当时我们不认识,无法坐下来商讨如何去对付那些批评;互相之间也不了解,并不知道我们在精神上已是多年的邻居。是外国人发现了我们的邻居关系。张晓刚在1993年完成的《全家福1号》,1994年就成为我的一本书的法文版封面,之后他的作品陆续出现在我的不同语种外文版的封面上,这些都是外国人的选择,不是我的选择,也不是他的选择。直到去年《文城》出版前,我第一次作出了选择,这时候我们已相互熟悉,于是《失忆与记忆6号》成为《文城》的封面。
此次上海龙美术馆的个展《环形剧场》展出的作品,是张晓刚这几年的最新成就。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我没有出国,除了回老家浙江海盐,很少离开北京,出门也少,张晓刚工作室是我这两年来最多的去处,那里像是朋友们的旅游景点,大家进门之后先上二楼转一圈,看看他的创作进展,然后回到一楼抽烟喝酒聊天。
与有些艺术家悄悄地创作不一样,张晓刚的创作过程是对朋友们开放的,这些作品里有的我最初看到的是素描稿,有的最初看到时只是画布上勾勒出来的线条,有的我以为完成了也搬走了,几个月以后又搬回来待在那里有待完成。当它们真正完成之后展现在我眼前时,我常常为之一怔:原来是这样。之前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觉得他也不知道自己葫芦里有什么药,他一边创作一边发现,最后打开了葫芦盖。
张晓刚高中时手抄过一句格言:人生就是几步而已。这句格言成为他后来的自我写照。
余华《在细雨中呼喊》:孤独与智慧交织的人生哲学
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被誉为其文学巅峰之作,歌手李健对此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所有人都应该阅读这本书。小说通过细腻的笔触,深刻地勾勒出人性的复杂与微妙,尤其是在独处、不争与远离这三种处世哲学上,展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真实面貌。这些主题如同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析了生活中那些不为人知的真相。
书中的主人公孙光林,自幼便被家庭所抛弃,孤独地在生活的边缘徘徊。他的选择独处,并非因为他天生冷漠,而是在亲人的无情和同伴的欺辱中,逐渐看清了人际关系的虚伪。在经历了种种痛苦后,孙光林意识到,与其在表面和谐的社交中消耗自己的情感,不如回归自我,守护内心的一方净土。在那个物质匮乏、人情淡薄的年代,独处成为他与自己对话的方式。在寂静中,他学会了洞察世界的真相,这份勇气与智慧是他对荒诞现实的有力抗争。
正如罗曼·罗兰所言:“在连绵不断的行动和感情的急流里,你们应该为自己保留一间单房。”这种独处的状态,让人们能够认清自己的力量与弱点,深入思考生活的意义。孙光林的故事提醒我们,孤独并非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内心的强大。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独处的时光可以帮助我们重拾自我,找到内心的宁静。
而书中提到的“不争”,则是另一种智慧的体现。孙光林目睹了父亲孙广才因小利争斗的惨烈结果,最终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这让他深刻认识到,争斗只会让自己陷入无尽的痛苦与疲惫之中。他选择放下争斗,放过自己,反而能够从生活的泥沼中挣脱出来。这样一种不争,并非懦弱,而是对生活荒诞与残酷的清醒认知。正如杨绛所言:“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在书中,远离也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人物苏宇的遭遇便是鲜活的例证。由于一次冲动,苏宇被推入舆论的漩涡,周围人的指责如同利刃,深深刺痛了他的心。在这样的情况下,远离那些伤害自己的人和环境,成为他保护自己的最后屏障。远离是对伤害的有力回击,是对自己尊严的捍卫。面对无法改变的恶意时,勇敢地选择转身,展现出一种智慧与勇气。
《在细雨中呼喊》展现了人与人之间充斥的冷漠、背叛与伤害。血缘亲情在利益面前显得脆弱无力,朋友之间的情谊在世俗偏见中也易碎得不堪一击。在这样的世界里,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许是一种“保护色”,让人在纷扰的尘世中守住内心的纯净,不被外界的污浊所侵染。独处、不争、远离,这三者构成了余华对人际关系的深刻思考,给予读者以启示:在生活的复杂中,保持一份独立与清醒,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挑战。
相关资讯
下篇:年年有余、九鱼呈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