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与谭正璧谈“中国女性文学”
▲1986年,谭正璧与其女谭寻接受笔者访谈
生于1901年的谭正璧,系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文学杂家。他著作甚丰,在没有电脑的年代,先后出版各类专著达150种,涉及文学史、小说史、戏曲史、历史小说等10个领域。谭正璧曾执教于上海美专、齐鲁大学、山东大学、震旦大学、华东师大,并担任棠棣出版社总编辑之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靠稿酬收入的他生活拮据。80年代初,他在施蛰存、赵超构推荐下,成为上海文史馆馆员。谭正璧年轻时患高度近视,后来视力越来越差,但其著述不断,精神可嘉。
最早知道谭正璧先生的大名,是笔者在卢湾区图书馆(今观复图书馆)书库工作时,偶然见到一本光明书局1935年版的《中国女性文学史》,虽只翻了几页,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又有机会读到谭正璧1930年出版的《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从中了解到中国历史上诸多女诗人、女词人、女文学家的创作经历。
1986年,我执编《新民晚报》“读书乐”专刊,便想请谭正璧先生谈谈他的读书得益。打听到他家住在南京西路润康村,便先打了电话,然后上门去约稿。
谭正璧的家在底层,约20平方米,除写字台、书橱与一张可两边拉开的西餐桌,室内还放了两张床,其中一张是折叠床。本来光线就不大好的房间由于堆满了各种书籍,书架上叠书架,直至天花板,环境显得凌乱而拥挤。他当时85岁,浓眉高鼻,满头银霜,让我意外的是他双眼已失明,幸亏他的女儿谭寻在旁。
我问:“谭先生,我想请教您怎么会对中国女性文学有兴趣的?”
不善言词的谭正璧说起这个问题时竟侃侃而谈:“没有女性就没有文学。早在《诗经》与《山海经》上就有女性作者写的诗作和‘女祸补天’的文字记载,人类活动最早就有女性参与,《载驰》便是许穆夫人所作。《诗经》中有好几种女性形象,如热情天真的少女,哀婉悲戚的怨女,温柔贤惠的淑女,刚烈果断的贞女,女性文学形象成为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主体。”
谭正璧又说:“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女性因经济地位低,她们的才情只能从男性统治的文坛上偶有突破。但尽管如此,《诗品》中评论20多位诗人之作,其中就有斑婕妤、徐淑、鲍令晖、韩兰英4位女诗人作品被点评。唐代出现鱼玄机、薛涛等女诗人,宋代文坛出现朱淑真、李清照这样有名的女词人。明清以来,女诗人、女词人、女弹词作家、女小说家不断出现。”
我说:“《水浒传》写了3位女英雄:孙二娘、顾大嫂与扈三娘,《西游记》写了诸多女妖精,《红楼梦》更是尽情渲染了‘金陵十二钗’,还有《镜花缘》写了‘女儿国’,您对这些文学现象,如何看待?”
谭正璧的普通话中夹杂着上海嘉定口音:“女性文学与女性形象在文学长河中展示其越来越强大的容量与魅力,我以为与时代发展有关,一是中国古代女子的才情在明清时越来越得以显示,清代女子写诗词、小说、弹词的人数大大多于唐宋;二是欧美妇女解放思想运动也在晚清进入中国,西方女性意识唤醒了中国东方文坛。”
我问:“在您从事文学的年代,当时曾出现了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梁乙真的《清代妇女文学史》,以及您撰写的《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3部书稿,这是对女性文学活动的最早肯定吗?”
谭正璧点点头说:“我想是的,谢无量先生著作出版于1916年,梁乙真先生著作出版于1927年,我写的《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则出版于1930年,他们两位谈女性文学,主要以女性诗文为主,我的著作虽出版在后,但我在此书中除评论女性诗词辞赋外,还增加以小说、戏曲、弹词等内容。”
我问:“您怎么会研究女性文学?”
谭正璧回忆道:“这可能与我早年经历有关。我出生于上海,7岁随祖母定居于嘉定黄渡乡,1919年考入上海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因新文化运动爆发,我边读书边写作,处女作《农民的血泪》于1920年发表于《民国日报》副刊。后由邵力子先生推荐,进入上海神州女校任教师,后又在上海务本女子中学任教。我这两段教师生涯,让我接触到不少有才情的女学生。在教书之余,我开始编撰著作,在撰写《中国小说发达史》《新编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家辞典》中注意到不少中国女作者的成就,这都让我对研究中国女性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我问:“您与当时的女作家有交往吗?”
谭正璧回答:“我最早接触的女编辑、女作家是白冰,原名陈淑媛,她当时编辑《女子月刊》,我曾向她投过稿,后来她改名莫耶,去了延安。20世纪80年代我曾与她联系,她已是甘肃省文联副主席。”
谭正璧说:“我在20世纪40年代参加过某杂志召开的一个座谈会,当时张爱玲、苏青、关露等女作家也在场,我和张爱玲都在会上发了言。不久,我又被邀请参加张爱玲作品《传奇》研讨会,我在会上对张爱玲小说中的心理描写表示赞赏,并认为她的中短篇优于长篇。”
我说:“您一直关注女性文学研究,是您首先提出中国女性文学吗?”
谭正璧纠正说:“不是,是梁启超先生首先提出来的,他于1922年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中第一个关注‘女性文学’,我受其启发,在1935年第三次出版《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一书时作了修改润色与订正,并易名为《中国女性文学史》。与‘妇女文学’相比,‘女性文学’更强调了女性的独立与自尊。”说罢,谭正璧让其女儿谭寻取出一本近年出版的《中国女性文学史话》(天津百花出版社1984年版)。
我说:“您一直把中国女性文学作为您一生研究的对象。”
谭正璧点头,他双目已盲,仍以口述而撰稿。
文:曹正文喜欢此内容的人还喜欢
原标题:《钩沉|与谭正璧谈“中国女性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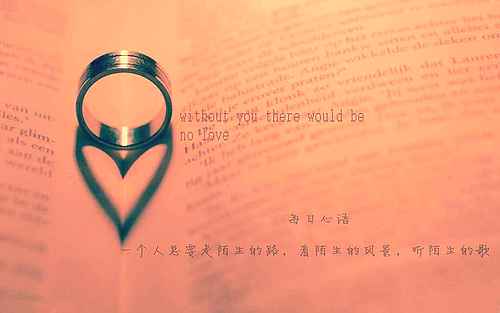
新女性写作的必然崛起:张莉对当代女性文学的深刻思考
在当今时代,女性的声音越来越被重视,文学领域同样充满了对女性经验和视角的探讨。这种文学现象被称为‘新女性写作’,它不仅是对女性创作的重新定义,更是对当代社会女性角色的深刻反映。张莉在《花城》中的工作,正是新女性写作的重要推动力。本文将围绕新女性写作的定义、特点,以及张莉的思考与创作,逐层剖析这一新兴文学潮流所承载的文化价值。
新女性写作,顾名思义,是新时代背景下女性作家的创作形式和内容的集成与创新。这一概念的提出,并非仅基于作品的年龄或作者的年轻化,而是对文学表现的重新审视与思考。
从2020年开始,新女性写作逐渐引起广泛关注,虽然它根植于更早的女性文学传统中,但以新情境和新审美迎接时代的转变,彰显了其与传统女性写作的区别。
新女性写作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内容更加多元,涵盖了关于身份认同、性别歧视和社会压力的主题;其次,在表达形式上,它更加强调个人的内心体验,语言的细腻与生动。最后,它推动了对于日常生活的深度探索,令作品充满真实感。
与早期女性作家的作品相比,新女性写作更加强调个人的独立性与主体性,试图打破传统的性别角色束缚。传统女性写作往往反映社会期待,而新女性作家们则通过文学表达个人的真实感受与反叛精神。
张莉在她的文章中对‘新女性写作’的定义和特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
她指出,‘新女性写作’不仅意味着新面孔、新故事,还包括对生活素材的独特理解与再创作。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观察,作者们能够提炼出具有普遍共鸣的主题,从而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
张莉提到了《那不勒斯四部曲》中的女性关系和成长故事,充分展示了如何通过个体的觉醒与成长来反映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在这一框架下,女性的声音不仅被呈现出来,也得到了更多的理解和关注。
张莉强调,在新女性写作中,日常生活的素材被赋予了新的意义。生活的不平常一刻、社会的隐秘关系,成为了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表现出女性桎梏与解放的双重体验。
通过分析几个重要作品,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出新女性写作的独特魅力。
4.1 《那不勒斯四部曲》的影响
《那不勒斯四部曲》中,莉拉与莱农之间的友情历程深刻反映了女性在社会中的成长与觉醒。故事通过细腻的个人体验,展现了女性在生活中逐渐消弭的界限,引发读者强烈的共鸣。
小说中,莉拉的三次觉醒展现了她对生活的深刻反思,尤其是在面对社会现实与历史变迁的时刻,使她意识到性别、阶级与身份的复杂性。
费兰特巧妙地运用简洁而富有层次的语言,让角色的经历和内心冲突得到完美的呈现。在这过程中,作品不仅关注个体成长,更引发对社会宽广议题的讨论。
韩江通过《素食者》展示的女性视角同样耐人寻味,书中描绘的家庭暴力与个人反抗深刻揭示了当下社会中隐秘的权力关系。
故事中,主人公的素食选择不仅是个人的饮食偏好,这一决定却在家庭中引发了剧烈的冲突,映射出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面临的压迫与不理解。
韩江以女性的视角挑战传统的性别角色,通过对日常生活场景的细腻描绘,令读者直面生活中的暴力与不平等,激发思考与共情。
在对比萧红的作品时,我们看到她同样运用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尤其是细腻又朴实的语言风格,无疑为新女性写作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萧红的《呼兰河传》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叙述,探索女性处境与家庭责任,为现代女性创作树立了标杆,而这种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依然在新女性写作中回响。
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新女性写作反映并影响了社会的变迁。
5.1 时代变化与女性文学发展
新女性写作不仅是文学现象,更是社会变迁的产物。随着女性地位的提升与社会观念的变化,文学作品中愈加频繁地出现女性视角的叙述,改变了历史上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传统。
5.2 新女性写作对当代读者的意义
对于当代读者而言,新女性写作展现了更为丰富的情感与真实的生存体验,使我们能够通过文学更深入地理解女性的声音与故事。这种共情的力量使得新女性作品得以在众多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产生深远影响。
新女性写作的不断崛起象征着文化价值观的转变,预示着女性在社会中日益增强的自我表达。这一文学形式以其清晰的声音和丰富的内涵,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
面对未来,新女性写作将继续探讨复杂的女性经历与广泛的社会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的书写将越来越多样化,呈现出更加独立而丰富的风格。
新女性写作不仅是对女性存在的再思考,更是对人类情感与经历的全面关照。它促使我们反思社会关系的本质,鼓励读者去探索我们所共处的世界。
女性在金庸文学中占据什么意义?
提起金庸,最先想起的可能是他笔下塑造的那些男英雄,令狐冲、张无忌、郭靖等等,随手一指,皆是经典。而女性在其中到底占据着什么意义?今年8月,中信出版集团推出新书《越过人生的刀锋——金庸女子图鉴》,对35位武侠奇女子的人生剧本展开探讨。作者六神磊磊接受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采访。
这是一本男作家隔着男作家的笔墨观察女性的书籍,也是六神磊磊这些年唯一一本关于女性的书,但却不是他单打独斗,而是团队作战。他直白坦诚原因:“一是因为署名作者一起参与了聊选题、碰撞想法,并且撰写了部分初稿;二是事先安排了两名女性小伙伴全程把关。”六神磊磊告诉记者,读书、写书若是能摆脱男性、女性的标签,则是最好,“因为探讨世界上存在的问题,除了两性视角以外,还有很多其它的视角。”
他是一名不折不扣的金庸迷,曾说过“我的三观底色是金庸奠定的”。于他而言,小时候金庸文学像是小孩子汹涌内心的代言,长大后变成了读者看世界的标尺,一个参照物。
如今总有人给武侠文学贴上“过时”的标签,然而六神磊磊发布在公众号上的文章,“黄蓉:谁稀罕当一辈子少女”“韦小宝的一种智慧:不争论”“再看阿朱:吃亏就吃在玩兴太大”……几乎篇篇阅读量达到10万+,大有粉丝在。
在金庸先生去世后,以六神磊磊为代表的武侠书迷,继续续写着一代人心中的江湖残梦。他以虚对实,借古喻今,既挖掘出那些江湖人物颠覆刻板印象的另一面,也似乎映照出现代人的所思所想、所困所惑。以犀利通透的文字和观点,向大众证明了一个道理:敢于直面真问题的文学永远不会被人遗忘。
以下文字,记者整理自与六神磊磊的对话:
1.为什么想到以女性角色为切口,写一本“金庸女子图鉴”?
在我们古代的文学名著里,经典女性群像是很少的。“四大名著”里只有一本《红楼梦》是认真写了女性的,另外三本都基本只讲男性。相比《红楼梦》中人,女性的存在只为了迸发刹那的光彩,炫目但短暂,最终只能被旧社会所吞噬掉。而金庸所塑造的女性则有更多可能性,比如说黄蓉、小龙女等。她们身处江湖,没有围墙,共同的使命是找到人生价值,也不依附于任何男性。
2.您在序言中提到说,这是一本成长的书,该怎么去理解“成长”二字?
这本书里精选了35位女性,但重点不是说我们一起来欣赏她们有多美。侧重点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书名“越过人生的刀锋”。所谓“成长”讲的就是她们每个人的成长。
毛姆有一本小说叫《刀锋》,刀锋指的是比较难的人生关口。我选择的35位金庸女性,不管是少女,还是人到中年的母亲,她们都各自遇到“刀锋”,因此掉入坑底,陷入误区。我在书里想呈现的就是她们怎么面对问题,从中摆脱出来的。
3.金庸小说里面,谁最贴合您心目中的“女神”形象?
金庸小说里有女侠,没有女神。他书里写的这些女性再出色再有魅力,也不是女神。每个人都带点小缺点,比如说你以为黄蓉很完美,结果发现她多疑,带有偏见;你以为小龙女很完美,又会发现她耳根子特别软,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这就是书中好玩的地方,包括他笔下的男性,也是如此。
4.男作家写女性,有困难吗?难在哪里?
很多成功的女性形象,有的是男作家写出来的,反过来,很多成功的男性形象,是女作家写出来的。张爱玲写男人写的入木三分,曹雪芹写女性写得灵气横溢。我觉得“写人”才是永远的难题,不存在男人写女人,还是女人写男人的问题。说起来,女人之间的区别,未必比男人和女人之间小。男女之间隔阂的不是性别,是人性。两性是人的标签,不用刻意夸大两者的对立和区别。
现在有些网络平台会把书分为男频和女频,喜欢看女频的读者,看男频小说,很难看下去,因为它是一个被定制的产品。读者想看什么,就会提供什么样的情节,但是金庸文学不是这样的,按照我公众号后台订阅的粉丝比例来看,男性和女性大约各占一半。所以说,经典文学一定能超越狭隘的定义。
5.“金庸文学是严肃文学吗”这个问题在网络仍然有许多讨论,您的观点是?
金庸小说里面,有些东西的确稀释了它的文学性,像大量的刀光剑影的打戏。但是讨论它是严肃文学还是通俗文学,没有任何意义。这两个分类也是一种标签,标签存在的意义太短暂了,它的概念和衡量标准都是会变的,随时会变。
6.现在有一种说法是,我们不再需要“武侠文学”了,您认可吗?
金庸文学里面所蕴含的侠气,不会被社会所淘汰。它本质上就两种东西,一个叫责任感,一个叫同情心。责任感是“与我有关”,同情心是“此事和我无关,但我关心”。无论社会怎么变化发展,这两种东西,社会肯定是需要的,以后也如此。
如果从文学阅读角度来说的话,这不只是武侠文学所面临的问题,整个图书行业都是,因为大众花费在深度阅读上的时间在减少。
7.金庸所塑造的那个部分架空的古代江湖世界,看似与现代世界大相径庭,可又好像有一些地方,能够与现代人精神相映照,这是为什么呢?
概括为一句话是,作家关注的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如果关注的是真问题,那么由此塑造的文学不会过时,它是有生命力的。有使命感的作家,应该尝试去解决一些重大问题、根本问题。
比如金庸所写的《笑傲江湖》,他要替令狐冲回答的是“要爱情还是要自由”。无论时间怎么变,可能每个人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再比如说,他故事中的女性,各自痛点不同,反映出的困惑也是丰富、多层次的,值得我们去解读。
一部文学作品,朝代虚构,人物虚构,背景虚构,最后呈现的故事有没有生命力就在于此。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见习记者 孙庆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