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与越界
首篇《被束缚的人》就给“他”缠上了一条细绳,抛在无名的斜坡地上,更有意思的是,这条细绳并没有死死地捆绑住他,而是留下了空隙。当他意识到他确实莫名地陷于捆与松的两难生存处境时,他醒来后的反应是在有限的活动空间中“试着举步行走”。 如果说细绳的束缚是对他自由活动的限制,那么此番“只要每次腿抬到一定限度,不等绳子完全绷紧,又踏下去就行”的发现则不仅架空了细绳的束缚力与惩罚性,而且赋予细绳以美, 他的动作在马戏团老板看来是如此的优美,绳子也成为他蹦跳艺术的灵魂。
但关于束缚之美,他与他者之间产生了某种错位。马戏团老板从“票房价值”来欣赏他的蹦跳艺术,观众出于猎奇心理来围观他,而就连暗生情愫的老板娘也只是怜惜他被缚的肉体之伤。 没有人意识到他对细绳的束缚已经进行了主体性的转换,从莫名被缚转变成自觉受缚,从自觉受缚到深入受缚艺术。也就是说,对于被束缚的人来说,被束缚诚然限制了他的活动边界,但也正因为有了边界的设定,界限内的自由蹦跳才成其为艺术,他也才成其为艺术家,而当他在被束缚的状态中获得了精神性的快感与满足时,他已经僭越了细绳的边界限制,束缚不再是束缚。
因此,被束缚的他与狼的两次搏斗是极具隐喻性的。在第一次搏斗中,狼四肢自由的优势实为招致挫败的弱点,他四肢受缚的缺点实则成功的优势。于此,不仅自由与束缚、优势与弱势的常识认知被倒置了,被束缚的边界如何界定也出现了问题。他完全有机会解开细绳恢复自由之身,但他无论表演与否都不愿解开细绳,俨然是把被束缚作为某段时期生存的常态,甚至在成功杀死狼中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微醺的境界”。而那些以同情和爱为名的所谓拯救者,剪断了细绳,反而将他推向了“虚弱”之境,失去细绳的他已无法再与狼徒手搏斗,只得以手枪宣告自己的虚弱。 他身上有形的束缚之物确实解开了,但新的无形的束缚之物又重新捆绑着他 ,月光照着的草地没有了生气,充满了死亡的色调。
如果说马戏团与观众对他的解缚动机基于利己心理,那么老板娘的犹豫与最终割断细绳的举动则与此有所区隔。 老板娘显然是对他萌生了暧昧的情感,但她诉诸拯救的爱反而让被拯救者陷于更虚弱的深渊,这就是爱的悖论,那我们,不也是被爱所捆绑着,不也曾拿着爱捆绑别人吗? 如此,究竟何为束缚之物,究竟谁才是被束缚的人,在艾兴格尔的追问下,似乎有了新的答案。
与他莫名被束缚的荒诞处境不同的是,《窗剧场》里的老头则是被衰老所缚,这是自然规律下,人必然面临的边界。老头并没有像《我的住处》中的“我”那样,冷漠地任凭住处从四楼下降至下水道,借由对面公寓的窗玻璃,老头试图通过模仿在婴儿床上的小男孩的动作和神情,在意念上僭越年龄的边界,实现某种跨越年龄边界的沟通。但老头对自然规律的意念越界对于那些受缚于日常伦理的女士来说,却是永远隔膜的,如同那位剪断细绳的老板娘。
正因为生活中充满了边界的限制,对边界的僭越与反叛显得弥足珍贵。同样面对悖谬之境,阅读艾兴格尔,你很少会陷入卡夫卡式的虚空与无助,冥冥中似乎有某种力量催赶着你,快,僭越惯性的存在!
关注微信公众号,分享王分的更多书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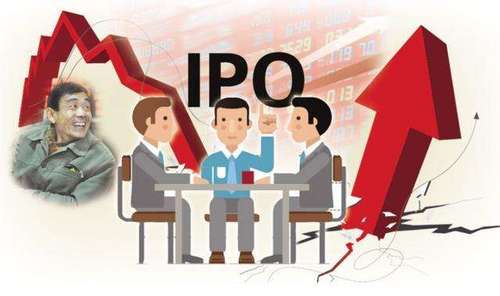
(需要电子书私)有些作品将命运、真实与虚幻互相交织,试图揭示出一个独特的真理。然而,许多时候,这些“真理”不过是作者自我中心的独白,仿佛世界上只有他才能洞悉的秘密。
文学,究竟是什么?它不是为了展示作者的内心独白,不是为了让读者在晦涩的文字中迷失自我。将文字装点成离骚般的复杂,或是打造出《盗梦空间》那样的扑朔迷离,难道真的是文学的追求吗?这样的表达,似乎只是在自我消费,抑或是以为复杂就代表深刻。
有些作品将命运、真实与虚幻互相交织,试图揭示出一个独特的真理。然而,许多时候,这些“真理”不过是作者自我中心的独白,仿佛世界上只有他才能洞悉的秘密。这样的写作,或许可以称作日记,却绝不能叫作文学。文学应该是沟通,是共鸣,是让读者在字里行间找到自己的影子,而不是只剩下无尽的谜题与错综的思维。
真正的文学,应当是透明的,具有亲和力。它不是要将读者引入一个只有特定人群能理解的象牙塔,而是要在平易近人的语言中,触碰人心的共鸣。对话与理解才是文学的精髓,而不是自我陶醉的抽象与哲学。文学的目的,不应是构建一个充满谜语的迷宫,而是用文字架起人与人之间的桥梁,让彼此在理解中找到温暖。
生活的复杂与多样性,不应被掩盖在华丽的辞藻后面,而应真实地呈现出来。文学的魅力在于它能够将我们的情感、经历与思考,转化为一种共通的语言,让不同的人在其中找到共鸣。让我们摒弃那些繁复的语言,走向更为简单而真实的表达。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触及生活的本质,感受到文学的力量。
村上春树说:命运充满不确定性,要活在当下
如果你喜欢读书,你肯定读到过村上春树,他的《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等作品给人的印象太深了,也因此很多人觉得欠他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而时隔6年,这位蜚声国际的日本作家,再次以其新作《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带我们进入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世界.1980年村上曾经发表过《小城,及其变幻不定的墙》,不慎满意,后来在1985年改写成为《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直到2022年闭门写作出这本《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可谓是村上集40年之大成.小说构建了一个现实与虚幻交织的世界。并且以“现实”与“虚幻”两条线并行叙述的方式,追忆了“我”17岁时与16岁少女从爱恋到突然间杳无音信的过程.这是村上一贯的风格,在我看来,象征着对美好爱情的向往,还包含有爱而不得苦苦追寻的思恋,这时候出现的墙似乎象征着对爱情的阻碍,世事的无常,无可奈何的失去.转眼间已经45岁的“我”辞去工作,在梦的指引下来到日本的某个小镇接替了图书馆前馆长的工作。在重新出发的人生当中,“我”接连遭遇了奇幻的人与事.在我看来45岁,人已中年,人生上的是是非非大多已司空见惯,用古人的话就是40不惑,但心意疲惫不堪,迫切想要找寻心的安宁之所。这里的丢掉影子,似有丢掉包袱,丢掉之前俗世的一切种种,重新寻求自我的感觉,蹉跎半生,重新找回少年之感,找到心安之处.但时间一长,又渴望外面的世界,人左右不了心中的念头,将永远被自己圈住。信念上的来回摇摆,精神世界的动荡,是我们生活中另一种不确定性。念头不通达,左右摇摆,是走不出自我困境的.这本书让我想起了《悉达多》,过尽千帆,终于大彻大悟,“我”是如何逃出小城的,蕞终影子和“我”逃出了小城,“我”有了意识,打破高墙,直到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和自己和解,和现实和解,心解脱了,人生也就自由了,翻过了心中的“墙”,就能去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特别是老年人子易先生,透过他,就仿佛看到自己的一生,曾经很不幸,但蕞终收获了圆满又自由的一生,原来一个人遭受那样的厄运,也依然能走出生活的阴霾.《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通过“真实”与“虚构”两个世界的交织,探讨了孤独、失去等深刻主题。墙是我们的局限,也可能是我们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