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古代中医,因为做人体解剖,被同行斥为“邪人”
中国传统医学对于人体构造的了解,深受《黄帝内经》等秦汉时期著作的影响。此后两千年间,除极个别医生因做过人体解剖,对脏腑位置有直接观察外,绝大多数古代医生坚持《黄帝内经》中那种阴阳五行和五脏六腑相对应的身体观,并不深究脏腑在人体内的真实情况。
在所有曾做过人体解剖实验的古代医生中,以王清任(1768~1831)最为著名。
王相信“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但在阅读中医典籍时发现,古书对脏腑的记述“处处自相矛盾”。 他于是将古人对脾、肺、肾、心、胃、小肠等器官的错误观点一一列举,如:
意即,有的书说两肾间的“动气”是命门,有的书又说右肾是命门,全无依据。
嘉庆二年(1797年)发生在滦州稻地镇的一场瘟疫,为王清任观察人体构造提供了机会。
当地很多草草掩埋的病故儿童,遭野狗撕咬,遍地“破腹露脏”。王清任每天去观察这些尸体:
唯一让王清任遗憾的是,因为尸体都曾遭野狗啃食,他没能观察到脏腑间的“隔膜”。
后来,王清任又三次到刑场观察死尸,也没能如愿看到“隔膜”。直至他的一位病人——曾镇守哈密、见惯死者的某官员,向王清任解释了有关“隔膜”的问题。
前后历时42年,王清任终于大体弄清楚了脏腑在人体内的情况。
他将自己所知的脏腑情况绘制成图,附在《医林改错》一书中,刊行于世。他自言:
他希望以后的医生能够参照脏腑图,更好地治病救人:
通过亲自解剖和研究,王清任纠正了《黄帝内经》《难经》等中医典籍里的很多错误。
他绘制的脏腑图,胃、肝等画的都比过去更加准确;脾由竖置改为横卧;隔膜被正确画出;肺上不再有“孔窍”;胰腺更是第一次出现……③
对于传统医学理论,王清任多有驳斥。
他否认所谓“三焦”的存在,第一次系统研究了“经络”的实质。通过解剖,他发现中医传统上所说“灵机在心”“心主神明”都是错的,真正产生意识、感觉的是“脑髓”,即大脑。
因条件所限,《医林改错》中也有很多失误。
比如,书中认为心中无血;将动脉当作气管;观察吸气、吐气、吐痰等和肺无关;把精道、血管、溺孔等绘为互通;把大肠(结肠)画的有如小肠(空回肠)等。④
王清任的研究方法,及《医林改错》中鲜明的正误共存,导致其人其书,在中国传统医学界饱受争议。
在抨击者看来,王清任可谓道德沦丧,嘉庆年间的名医陆九芝说他是:
清代儒医陈年祖也指责他“不仁”,乃“狂徒”“邪人”。⑤
当代中医,多认为王清任“越改越错,错中加错”,如名医蒲辅周说他:
中国传统医学,长期以来仅关注脏腑功能,而不在意脏腑形态;研究人体,依靠的是阴阳五行学说,而非实体观察。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很多古代儒医认为,并不需要借助解剖实验来认知人体;王清任的努力,也因此在他们眼里变得全无意义。
王清任通过解剖观察脏腑,并敢于质疑《黄帝内经》《伤寒论》等传世经典,使 《医林改错》成为中医学突破阴阳五行哲学体系,走向现代化的先声
最早汇通中西医学的陈定泰,正是在王清任及《医林改错》的启发下,参考西方的解剖图谱,才绘制出较为精确的“脏腑全图”。
时至今日,学术界对王清任的肯定,已更多地集中在其科学实证精神,而非苛责其《医林改错》本身也存在不少错误。如谓王清任:
可惜的是,王清任的科学实证精神,并没有能够被后来的中国传统医学所继承。
一是如前文所说,当时主流中医从伦理上鄙夷王清任的解剖实验,且坚信《黄帝内经》等经典著作,不认为中医发展要借助解剖。
二是王清任出版《医林改错》后不久,西医著作就大规模传入中国,学习解剖及脏腑的相关知识,直接阅读水平更高的外国著作即可。⑩
于是,在《医林改错》中,只有居于次要地位的“逐淤活血方药”,因为切合中国传统医学的气血理论,仍被中医沿用至今,王清任其他更重要的学术遗产,反被长期湮没。
王清任万万不会想到,在他过世一百余年后,《黄帝内经》及其荒唐的“阴阳五行”理论,依旧被中国传统医学界奉为圭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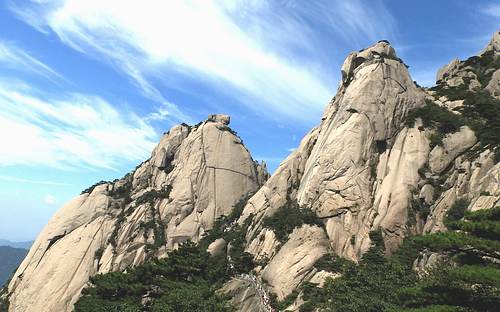
古代结婚,用被有什么讲究?
东方网-东方头条消息,在寒冷的冬天,夜里上床睡觉,拥有一床大大的暖暖的被子,是再舒服不过的事情了。
被子在现代人看来是很普通、也不值钱的睡眠用具,但在古人眼里却是重要的“家当”,是财富象征之一,被子大小也显示一个人的家庭地位如何,受不受尊重。
《梁书·裴之横传》(卷二十八)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曾任吴兴太守的裴之横,少年时不学好,用今天的话来说,整天不做正业,鬼混。其兄裴之高为了激励他,有意做了一床不宽的小被子给他盖,并且只给他吃蔬食。裴之横发誓:“大丈夫富贵,必作百幅被!”后来,裴之横果然发达了,真的做了一床百幅宽的被子。
如此大的被子可谓“古代第一被”,放在今天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只是不知道这么大的被子怎么盖?但被子的功能是保暖,有条件的尽量做大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在实际中也是这么做的。
在大小上,古人结婚用被便很讲究,除了用料好外,被幅都不小。古人为什么要将婚被做得大一点?因为是双人用啊。过去小夫妻都睡一被筒里,而不像现代,不少新婚男女同床分被窝,说是卫生,还不影响对方休息。但即使各睡各的被窝,在双方需要做那种活时,还得钻到一个被窝里,被子过烛身子会露出来的,不只尴尬,还容易受凉,所以,现代的婚被也不小的。
古人结婚少不了要陪婚被的,新娘嫁妆中陪被子,新郎婚床上置被子,即便在夏天结婚,也要准备好秋天要用的被子。
有条件的人家,被子用绫罗绸缎来做,所谓“锦被”、“绮被”、“罗被”都属于这类高级被子。据宋李昉《太平御览·服用部九》(卷七百零七)引《东宫旧事》,晋太子便有“七彩文绮被,又有绛文罗被”。
太子结婚时要准备:“彩柸文绮被一、绛具文罗一幅被一、绛罗文绣四五幅被一。”(另据《太平御览·皇亲部》(卷一百四十九)“太忆妃”条引《东宫旧事》,晋朝太子纳妃结婚时要准备被子:“绛真文罗一幅被子一,绛罗绣四幅被一。”)
结婚用被因为都是双人被,又叫“鸳鸯被”、“合欢被”,文雅一点的称为“鸳衾”。东汉《古诗十九首》中有一首《客从远方来》这样写道:“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
从古诗中可以知道,被子在古代男女生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汉刘歆《西京杂记》(卷一)记载,赵飞燕在当上汉成帝刘骜第二任皇后,她的妹妹送了一批高档用品,其中就有“鸳鸯被”、“鸳鸯褥”。
古代最著名的一床鸳鸯被,大概是后蜀主孟昶的。
据元陶宗仪《 南村辍耕录》(卷七):“鸳衾,孟蜀主一锦被,其阔犹今之三幅帛,而一梭织成。”陶宗仪之所以记下孟昶这床鸳鸯被,是因为这被子制作特别,古今仅见:“被头作二穴,若云版样,盖以叩于项下。如盘领状,两侧余锦则拥覆于肩。”
把被头挖成衣领样,盖身上时刚好露出两头,这种夫妻双人被设计,很符合人体工程结构,既特别,又温情,是不是很有意思。
(原标题:古代结婚用被有什么讲究?)
被排斥与被神化的中国古代外科手术
“越人救虢太子于既殒,胡医活绝气之苏武,淳于能解颅以理脑,元化能刳腹以浣胃,文挚愆期以瘳危困,仲景穿胸以纳赤饼。”
不妨尝试揣摩葛洪写下这些文字时候的心态:他是以这些医术为医道高妙之象征,以上六条医家奇能中涉及外科术的有四条,足可见葛洪心目中医家以外科为神奇。
外科之神奇来源于其神秘和高难度,在六朝隋唐时期,外科术已经变得体表化、小型化,并且被排除在主流医道之外,但是上古时期并非如此。
有关外科手术的发展历史,李建民《华佗隐藏的手术——外科的中国医学史》及笔者《被怀疑的华佗——中国古代外科手术的历史轨迹》已经有所阐述。
2001 年在山东广饶傅家村大汶口文化遗址392 号墓发现的一个颅骨,证明5000 年前我国已有开颅手术;在新疆鄯善县苏贝希村曾出土2500年前男性干尸,腹部有刀口,以粗毛线缝合,很有可能是腹腔手术;至于华佗外科术,更是家喻户晓。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解剖学的极度不发达和初期阶段外科手术的高风险性,导致外科手术逐渐被中国主流医学所抛弃,至少自南朝开始,医界就开始将华佗外科术排除在“正道”之外。
“春秋以前及和缓之书蔑闻,道经略载扁鹊数法,其用药犹是本草家意,至汉淳于意及华佗等方,今之所存者,亦皆备药性,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宗,又悉依本草,但其善诊脉,明气候以(意)消息之耳。至于刳肠剖臆,刮骨续筋之法,乃别术所得,非神农家事。”
陶弘景之语耐人寻味,“非神农家事”一句将华佗以及传说中的扁鹊等人外科术排除于医道之外,“别术所得”似暗指此乃巫觋之术,占卜施法常被称作“方术”,医药往往也在其中,但是陶弘景将两者并列,故可排除医道,似专指巫觋,亦即非人力所能致。
此后古医家对待华佗的态度基本上是承认其医药神效,但基本不承认其外科术真实性。例如唐代孙思邈对于华佗外科术采取的态度是不置一词,《千金方》中虽然大量引用华佗方,但是却不涉及外科术,
《千金方·序》中如此概括华佗:
“汉有仲景仓公,魏有华佗,并昏探赜索隐,穷幽洞微,用药不过二三,灸炷不逾七八,而疾无不愈者。”
此话有意回避了外科术,但是由此博得了北宋校正医书局馆臣们的一致好评,
“我道纯正,不述刳腹易心之异;世务径省,我书浩博,不可道听途说而知。”
孙思邈在这个问题上的价值观代表了隋唐医学家,观此时医书引用华佗及其弟子医方者甚多,但是却均对外科术失声,可见在医家心目中此事近乎荒谬。
但是这并不妨碍唐代民间对华佗的崇拜,张雷指出:“大约在唐开元中,亳州就已经建造了祭祀华佗的庙宇,神小而庙微,又以尼姑主持,故名‘华祖庵’。宋代,地方开始有华佗庙的修建。”这种崇拜当属于民间淫祀,但却依托于佛教框架内,是中国本土信仰功利性和多元化的体现。
对华佗的怀疑,除了不信之外还有神化。例如
梁萧绎《金楼子》卷五《志怪篇》:
“夫耳目之外,无有怪者,余以为不然也。水至寒而有温泉之热,火至热而有萧丘之寒。重者应沉而有浮石之山,轻者当浮而有沉羽之水。淳于能剖胪以理脑,元化能刳腹以浣胃。”
“(华)佗之熊经鸱顾,固亦导引家之一术,至于刳腹背、湔肠胃而去疾,则涉于神怪矣。”
亦有将华佗技能看作是天赋异禀者,
“华元化医如庖丁解牛,挥刀而肯綮无碍,其造诣自当有神,虽欲师之而不可得。”
“世传华佗神目,置人裸形于日中,洞见其脏腑,是以象图,俾后人准之,为论治规范。”
华佗何以能“刳肠剖臆”?因为华佗“造诣自当有神”或有“神目”——这就是二文对于华佗的“能”与后世的“不能”之原因的解释。应该说对华佗外科手术的“神化”过程本身是一个“去人化”的过程,即将曾经实际存在的腹腔外科手术看作是非人力所能致,将华佗这个实际存在的人物涂抹上神异色彩,究其根本,这是对胸腹腔外科手术的另一种怀疑。
对外科术的神化就是这样,它出自对外科术的惊奇,夹杂着主流医家的否定和民间的崇拜,但归根结底是外科术没落的体现。
(摘自《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于赓哲著,中华书局2020年6月出版)
十年磨一剑,于赓哲教授医学史研究新著。
跳出线性进步主义史观,还原传统医学真正样貌。
历史学家的探索和思考,是否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启示?
《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
978-7-101-14525-0
古人如何面对瘟疫?瘴气是真实存在抑或只是出自人心的幻想?古时候的医患关系是怎样的,他们也有医患矛盾吗?于赓哲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中古时期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认为“疾病比很多因素更能长远影响人类历史”,“在摸索人与社会甚至人性的基本规律的时候,医疗与疾病是一个绝佳的窗口”,本书通过对海内外大量史料的爬梳整理,剖析实际案例,探索疾病与人心、医疗与社会、中医与西医之间的关系,尝试发掘文字背后隐藏的史实,并提供一种思路,试图将传统医学从“科学还是迷信”的窠臼中拉回来,还原中国古代医学本来面貌。其切入点既有医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医者形象的模塑、医患关系的探讨,亦有对古代的卫生体系、瘟疫致与治的思维模式、性病对青楼文化的影响、宋代墓葬壁画背后的医药文化等问题的思考。
原标题:《被排斥与被神化的中国古代外科手术》
相关资讯
那些隐藏的、埋藏的宝藏仍在世界各地被发现
那些隐藏的、埋藏的宝藏仍在世界各地被发现每个小孩都梦想找到被海盗或古代国王藏起来的埋藏的宝藏。虽然成年人可能会放弃这些异想天开的梦想,但对于冒险家来说,所有的希望都不会失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