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里为何常见“登高凭阑”
《幸福票》 刘庆邦华语短经典(第二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如何写短篇小说?直接复刻生活,或从长篇小说中截取一段行吗?作家刘庆邦最近出版短篇小说选《幸福票》,他说,短篇小说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它的虚构性,在现实故事结束的地方开始小说意义上的故事,主要写的是尚未发生但有可能发生的故事,是创造一个新世界。短篇小说创造的这个新世界什么样?他又说,写的是日常烟火,家常冷暖,越是离奇的东西反而越构不成小说。事情再稀奇,再古怪,里面如果没有短篇小说的种子,一切都是白搭。那么,什么是短篇小说的种子?在他看来可能是一个细节,一种思想;也可能是一句话,一种氛围,是一段曾打动过我们的生活。
我觉得写短篇小说要有短篇小说的精神。这种精神我认为一是对纯粹文学艺术的不懈追求;二是和文学商品化的顽强对抗。
经常接触一些文学刊物的编辑,他们说现在好的短篇特别少,要发稿了,总是找不到够水平的精彩作品。短篇小说是一种更接近诗性和神性的文体,它藏不得拙,遮不住丑,掺不了假,考验的是作家的真功夫。特别是目前在小说批量生产的情况下,短篇小说显得更加珍贵。短篇小说的存在,证明着小说文学性的存在。莫言也说过,现在应该是短篇小说的时代。可现在写短篇小说的却越来越少,写长篇大套的却很多,用他们的话叫“扬长避短”。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太合适,容易造成误会。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长篇和短篇各有千秋,谁都代替不了谁,好比瀑布代替不了大海,大海也代替不了瀑布。
短篇小说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它的极端虚构性。主要写的是尚未发生但有可能发生的故事
短篇小说是一种独特的文体,有着独特的选材取向、独特的肌理和结构方法。长篇小说那么一大块东西,我们从上面取下一块,当成短篇小说用行不行呢?我的看法是不行,性质不同,狼皮是贴不到羊身上的。短篇小说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它的虚构性,极端虚构性。它是在现实故事结束的地方开始小说意义上的故事,是在看似无文处作文。它主要写的不是已经发生的故事,而是尚未发生但有可能发生的故事,是创造的一个新世界。汪曾祺评价林斤澜的短篇小说,说“无话则长,有话则短”,就是这个意思。短篇小说在现实生活中,只取那么一点点东西,这一点点东西,我称之为光点,或短篇小说的种子。以光点照亮现实,用种子生发小说。种子是世间万物生生不息、传宗接代的东西,有了种子的传递,世界才延续下去。我喜欢种子这个词,它就给人以饱满、圆润、美好的感觉。
有可能生长成一篇短篇小说的根本性因素,这是我给种子下的定义。种子有了,小说就有了出发点和落脚点。短篇小说生长于心,用心灵的土壤培育过,心灵的雨露滋润过,心灵的阳光照耀过,才有可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生长成一篇美好的小说。种子饱满,情绪就饱满。我自己对这样写出来的小说也挺喜欢,一看就想看完。我的小说不是发表了就完了,我还会看,常常看得自己眼湿。
有人说短篇小说是生命之缘,可遇而不可求。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求,只有求,不断地求,才有可能遇到它。否则就有可能失去相遇的机会。以前我在报社工作,经常去矿上走,有的朋友知道我业余时间写小说,主动给我讲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我不拒绝朋友的好意,但事情再稀奇,再古怪,里面如果没有短篇小说的种子,一切都是瞎搭。再说了,小说写的是日常烟火,家常冷暖,越是离奇的东西越构不成小说。
短篇小说的种子可能是一个细节,一种思想;也可能是一句话,一种氛围。有一段生活,曾打动过我们,让我们难以忘怀,隐隐觉得里面有短篇小说的因素,却迟迟不能动手写。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就是没有找到种子所在。等到有一天,我们发现了种子在哪里,会感觉豁然开朗,好了,小说可以动笔了。
没有思想参与的感情是肤浅的感情,只有思想之美和情感之美相融合,感情才是厚重的、有质量的感情
我认为小说的主要功能不是讲道理的,是讲故事的,是表达情感的,是审美的。但小说又是理性的果实,需要思想的引导和思想的提升。没有思想参与的感情是肤浅的感情,只有思想之美和情感之美相融合,感情才是厚重的、有质量的感情。
我们写小说的过程,就是处理和现实关系的过程。不管我们和现实的关系如何,我们的写作仍离不开现实生活。如同人的梦离不开人的生命,树的影子离不开站立的树木,我们的想象也离不开现实生活的基础。现实是作家的根本处境,也是作家不可摆脱的命运。然而光怪陆离的现实生活也有着相当强的诱惑力和纠缠力,它们仿佛一再拦在我们面前,说写我吧,写我吧,我是很时髦的,很刺激的,很有卖点的,写了我,保你不会吃亏。如果我们稍不清醒,就有可能被缠上,掉进它们为我们设下的陷阱。
有人说,现实生活太丰富了,太精彩了,作家用不着虚构和想象,直接把现实生活拿过来就成小说了。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我们的创作和现实的关系是一种利用和被利用、纠缠和反纠缠、摆脱和反摆脱的关系,是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我们对现实照搬不行,追赶不行,紧逼也不行。不管现实生活怎么样,照搬过来都不符合小说艺术上的要求。我们要把生活经过消化,沉淀,变成一种回忆状态,以便用心灵化、诗意化、哲理化的眼光对现实生活进行观照,使其上升到美学的层面。
方法再多也要从生活中、记忆中取得种子,然后全力加以培养,使之生长壮大起来
我们听到多种关于短篇小说的写法,有建筑法、控制法、平衡法、编织法等,比较多的一种说法是说短篇小说要用减法来写。这种说法有针对性,有一定道理。把好多情节、人物、细节等,往短篇小说的口袋里装,撑得满满的,没有一点空间,于是产生了减法说。我不太认同这种说法,觉得这是一种机械的、生硬的、武断的说法,起码不是那么准确。我认为短篇小说应该用生长法来写。生长法是道法自然,也是投入自己的生命,从生活中、记忆中只取一点点种子,然后全力加以培养,使之生长壮大起来。或者说一开始只是一个细胞,在生长的过程中,细胞不断裂变,不断增多,不断组合,最后就生成了新的生命。
我比较笨,写短篇小说下的多是笨功夫。比如一篇小说写到要紧处,觉得有一个好细节才撑得起来。我甚至用字数来筹划,此处要写够一千字,或两千字,小说才会饱满,充分,然而有时遇到了困难,写不动了。这怎么办?这时我决不偷懒,决不绕着走,而是咬着牙奋力想象。想象力是我们创作的主要生产力,任何作品的创作都离不开想象力的发挥。而人的想象力通常不是一种显力,是一种潜力,需要我们像在矿井下打巷道一样奋力开拓,想象的潜力才能挖掘出来。我写短篇小说《鞋》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写着写着写不下去了。我坐在桌前,坚持着,劳动着,想象着,灵感突然爆发,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细节。这样坚持的效果给人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回忆起来,我的不少小说的神来之笔都是来自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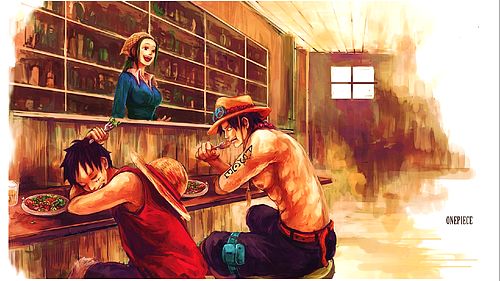
胡腾:看不见的现实
胡腾短篇小说《迷楼》刊载于《花城》2020年第3期,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即可购买纸刊。
Benigno Hoyuela
朋友木叶在某篇文章里写道,一个作者独特与否,全在于他眼中能否有“看不见的现实”。我实在喜欢这个概念。
试想陶渊明,究竟在做官时,还是辞官隐居之后,才开始触摸、书写、甚至发明独属于他的现实?我想应该是后者。不管是在书斋里读《山海经》,还是去东篱下采菊,或者悠游于虚无缥缈的桃花源,他都比同时代的其他作者更接近某些更重要的“看不见的现实”。也许,对于一个作者,身处何地远没有心处何地那么重要。心改变了,身体自然会跟着动,看到的、听到的、大脑中为之疯狂的,多半就是和以前完全不同的现实。
站在作者立场,这个写作和现实的问题,可能是非常单纯的。或者出于机缘,或者跟随内心冲动,他会选择到某个触摸世界的独特角度。无须特别费力,自然而然就会得到。得不到,也没有任何办法。
对于一个写作/阅读/传播的系统来说,这个问题才真正变得复杂。因为一切都需要时间,需要足够的条件。陶渊明若刚一辞官,便贫病交加,很快一命呜呼;又或者,他写下的文章诗稿,在一场火灾中化为灰烬;再比如他临终将自个儿文字托付给某个朋友,却遇人不淑,终于洇灭不闻——那么,我们根本就不会有机会来讨论,所谓陶渊明发现的现实。
换句话说,卡夫卡可能是根本不为我们所知的。但文学史上,肯定会有一个起到类似卡夫卡作用的作者。
从数学上讲,这就是个概率和风险的问题。越独特,风险也就越大。但是为了那种独特,怎么样的风险也是值得的。
就说高更和梵高这两个人。他们所发现的“看不见的现实”,又被后来者再次看见,才得以传播开来。比如毛姆写《月亮与六便士》,简直就是高更跨越时空的亲密战友。他后来又写《刀锋》。有人说主人公原型是维特根斯坦,我倒觉得更像梵高。这篇小说没有一个字写纳粹,里面的众生相,却无法不使读者想到和小说文本同时代的纳粹——太多的人为生物和社会的双重基因所困,才甘愿随波逐流,听任极权对自己为所欲为。但无论何时,总有像梵高(维特根斯坦当然也是)那样的不入流者、彷徨者、质疑者,这些怪胎的精神世界像一面魔法镜,将我们习以为常的坚固现实照出了分崩离析的影像。
存在“看不见的现实”,也是因为,那种现实远远超越时空的限制。比如曾做过维特根斯坦学生的图灵,出于对老师语言哲学的本能质疑,在可计算数的概念性世界里看见了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前景。我不太赞同《三体》中的黑暗森林理论,但猜疑链上那个最重要的前提,技术爆炸,我是绝对支持的。爆炸绝不只是烟花绽放的那一刻。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风起于浮萍之末。在某个洪荒星球上发现一个细菌,就能想象到若干亿年后出现的璀璨文明:这才是真正要紧的现实。现实是过去,也是未来。截断观察,现实不一定鲜活跳动,甚至死气沉沉也有可能。但整体观照,现实一定是诡奇壮丽,让人心潮澎湃的。
就像《桃花源记》中那简简单单一句: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信奉文学乃人类头脑中的黑暗触角,往可能多的方向生长,以探索自身和宇宙的边界。每个作者既是孤独的,也永远以其他人类的创造为参考坐标,寻路不已。
本期点评:故土,亦是新地,文学何为?/ 何平
关于《最后的远握》 / 刘文飞
——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间的最后十封书信
哔哩哔哩:一种“表达赋权”的可能
面对这片土地,也面对生活的现实
——中央电视台纪录片《花城》访谈实录
展现极端环境下的人性光辉读张贤亮短篇小说《灵与肉》
> > >
展现极端环境下的人性光辉——读张贤亮短篇小说《灵与肉》
时间:2024-05-13 10:52
《灵与肉》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张贤亮的代表作之一,亦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部重要作品。作者以自己在西北地区二十余年的现实生活经历为蓝本,通过讲述知识分子许灵均在经历了下放到农场放马和艰苦生活的过程中与善良淳朴的普通劳动者接触,在精神和肉体的磨砺洗礼中得到升华的故事,探讨了道德、爱情、自然等诸多问题。
张贤亮以其独特的个人经历和社会背景为基础,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中人物及社会的深层价值关系,同时通过深刻的人文关怀和细腻的心理描写,展现了人物在极端环境下的人性光辉和精神追求。
在《灵与肉》中,张贤亮通过对个人命运和经历的细致描绘,反映主人公所处社会的现实状况和对人性与理想的深刻思考。如在许灵均与李秀芝的恋爱故事中,展现了爱情的真实与纯洁,向读者传达真正的爱情可以超越物质条件的限制,可以抵御时间的侵蚀和利益的诱惑,是两个人之间心与心的双向奔赴,给予精神以慰藉,给予生活以动力。在父亲为他们全家提供美国生活的机会时,许灵均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留在他用汗与泪浸润过的土地,这是爱国主义的真挚体现,也是对知识分子人格的深刻理解。
张贤亮擅于挖掘人物内心世界。“唯其有痛苦,幸福才更显出它的价值。”这是小说《灵与肉》中令我非常震撼的一句话。一个拥有纯粹灵魂的知识分子在回首往事时,那些经历了许久的苦难和痛苦似乎不值得多提,而来自辽阔草原最淳朴的底层劳动人民的理解和温暖,才是弥足珍贵的东西。许灵均的精神在所遇到的苦难中,在自我审视下,不断崩塌、分解、更新,渐渐重构起一个心灵世界,重新塑造出人格形象,于此,方能铸就趋近于完美的灵与肉。
《灵与肉》寄托着张贤亮对知识分子精神升华的人文关怀。在作品中,他将肉体温饱和精神温饱进行极致化的表现,尖锐的矛盾尖锐迫使许灵均、迫使作者、迫使读者进行抉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享受人对自然的敬畏和依赖,会在困难与磨炼中找到生活的勇气和价值,会由衷地对劳动人民的质朴正直致敬。我想这就是许灵均最终选择留在草原、留在劳动者身边的原因吧。
苦难从来不值得歌颂,但在苦难中展现的人性光辉,值得久久褒扬。2024年是张贤亮逝世10周年,《灵与肉》也迎来了发表的第44个年头,张贤亮在《灵与肉》中所探讨的人性本质和道德底线是不受时间和空间约束的。作者通过许灵均的故事,让广大读者认识到,无论岁月如何流转,无论社会如何变迁,一个人所具有的尊严、良知、道德等精神品质,都是不可撼动的。
相关资讯
迟子建《东北故事集》: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与纠缠
小说中的隐形主人公罗振玉,其实在迟子建二十多年前的小说《伪满洲国》时就有所涉及,2019年,迟子建去到罗振玉旧居,听旅顺博物馆的专家讲述当年罗振玉所收藏的文物(尤其是甲骨)失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