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写实主义
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文艺创作出现的一种新的创作方法 种创作现象,新写实主义有别于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作品的艺术风貌。新 度上淡化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追求描写生活的"原生态", 竭力隐蔽作者的主观感情和思想倾向。新写实主 过他们都竭力淡化社会阶级关系和政治 历史背景,避开重大的矛盾冲突与斗争,致力于描写生活琐事、性爱 因如此,"新写实主义"很难产生视野恢 宏的反映现实的伟大作品,其艺术视 作品对现实负面现象的揭露与批判,笔触 画的事件与人物也有一定的典型意义,这种探索与创新无疑丰富了我国文学的"百花园地"。但这类作品对生活取材的偏 ,使作品的主题缺乏亮色和积极进取的 0年代的建设四化的伟大斗争和改革开放中,"新写 在不断扩大自己的生活视野,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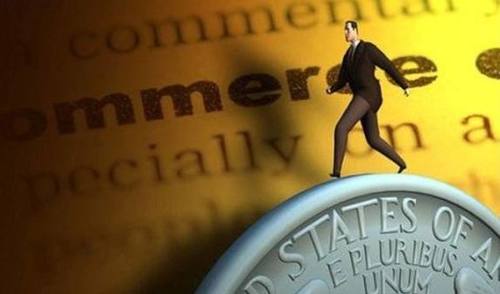
许春樵:先锋小说艺术的迷恋者
周新民:许老师你好!1990年代初期小说创作呈现出与80年代小说创作完全不一样的面目。评论家认为,20世纪90年代先锋小说开始退潮。你大概是这个时期走上小说创作道路的。你对1990年代初期的中国小说创作状况是否有自己的评价?
许春樵:我对1990年代初期的中国小说整体感觉是:在经历了先锋文学虚妄的狂欢和假象的繁荣之后,中国小说正在大踏步地回归理性与常识。后来,我发现,西方现代派文学对中国文学最大的意义,仅止于对中国叙事传统的刺激与改造。
包括我在内,不少中国作家在风起云涌的先锋浪潮中悟出了小说写作在白描与写实之外,还有心理感觉与心灵体验等无限丰富的形式的可能性,而像卡夫卡、加缪、福克纳、乔伊斯、普鲁斯特等所凸显出现代哲学语境下的精神性写作,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国是没有基础的,或者说压根就不存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更没有实现现代化。
所以中国那批现代派先锋作家基本上都属于模仿性先锋,技术性先锋,而不是具有现代精神性质地的先锋。
当所有刊物的编辑连天加夜地开始阅读他们根本读不懂的普鲁斯特、格里叶而唯恐落伍时,当中老年作家们也忍不住模仿乔伊斯、韦斯特的时候,误区就出现了。因为现代派文学实际上已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价值,传统的写作被一种自卑和落后的情绪所包围着,这直接导致中国先锋文学不是借鉴而是照搬,不是参照而是克隆,文学的基本规则和文学的基本要素在这场不讲原则的模仿大潮中被严重颠覆。作家和评论家一直对此不敢或不愿做出果决的反思与质疑,唯恐背上抱残守缺顽固不化的名声,这种过度模仿后的贫血与苍白造成了先锋文学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迅速衰落,《钟山》在1989年第3期最先亮出“新写实小说”的旗号,并与《小说家》等刊物拉开了“新写实小说大联展”的序幕,这是一次对先锋小说主流化的公开反击。于是1990年代初出现了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单位》、刘醒龙的《凤凰琴》《分享艰难》等小说在先锋文学的阵地上强势突围,并大获追捧。
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那些红得发紫的先锋作家们从刊物上和读者们的阅读视线中前赴后继地消失了,在格非、苏童、马原、孙甘露之后出现的一批新锐的先锋作家如李冯、张生、朱文等一批人,尽管他们比前辈们感觉更好,理念更新,但再也没有多少评论家追捧了,他们艰苦卓绝的努力理所当然地失去了轰动效应,也失去了众人喝彩的场景,他们过着寂寞而清贫的生活并等待着一些无法出现的奇迹根本不可能发生。
1990年代初期是中国小说的转型期,从先锋回归写实,从非常回归正常。
周新民:与先锋作家转向不同的是,你在1990年初期的小说创作执着于先锋小说艺术探索。你能谈谈你在《季节的景象》《季节的情感》和《季节的背影》这三篇小说中的艺术探索么?你能具体谈谈你当初的设想么?
许春樵:《季节的景象》《季节的情感》是在华中师大读书时写的,《季节的背影》是毕业后写的,分别发表在《上海文学》《萌芽》和《山花》上,这是一个“乡村系列”的小说。严格说来,这不是一个先锋系列的小说,但有先锋的影子,有先锋的意味。这组小说的先锋性不是体现在精神层面,而是体现在小说叙事上。当时我们学了一大堆“新批评”、“叙事学”、“俄国形式主义”等方面的东西后,我就在宿舍里开始研究小说叙事的“陌生化”, 1990年秋天的某个黄昏,我很幼稚而激动地跟同宿舍同学宣布:“‘陌生化’的办法找到了!将非经验的抽象感觉形象化,将经验的形象叙事抽象化,从而造成双向反讽式的叙事张力。”于是《季节的景象》里就有了这样一些句子,“榆儿在一个天空飘着微雨的清晨离开愤怒的父亲和繁茂的庄稼,她孤身一人走在乡村古老的目光里,听到了水牛啃草的声音正在漫过田野。”“在秋天残余的日子里,荷子读了一些描写北方的小说,知道此时的北方已经开始下雪,一些北方的故事在冰天雪地里进行。”这些叙事中还包含了我的一些理性妄想,诸如“情境的不合理配置”、“时间与空间的变形”、“细节的放大与收缩”等。
《季节的景象》被《新华文摘》转载后,又获了“1990—1991《上海文学》奖”,在浙江领奖时,《上海文学》主编周介人先生对我说,评委中复旦大学的一位老先生对我的小说叙事有异议,是周介人竭力推介,才投了赞成票的。今天看来,那一组小说中,叙事很出位,很新鲜,但由于用力过猛,所以许多地方显得雕琢而做作。不过,整体上的情绪控制和人物把握还算是准确而到位的。
现实品格与艺术热情的融合
首先,强烈的现实感和批判性,人文精神烛照下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是湖北中篇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无论是上世纪90年代早期池莉、方方等的新写实小说,还是此后陈应松、刘继明等更为注重形式探索的小说,无论是晓苏等的反讽解构小说,还是邓一光的具英雄主义色彩的小说,虽然各自在题材、主题、艺术手法上都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性,但在其背后,那种勇于直面惨淡人生、不矫饰、不做作、坚守人文理想高地的文化精神和文化逻辑却清晰可见。其中,池莉、方方、刘醒龙可为代表。
池莉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她的艺术世界执著于市民化的生存时空,在这里,普通人的命运、人生历程、基本需求、欲望与困惑、喜怒哀乐是她关注的重点。不过,从她的《烦恼人生》到《来来往往》,再到《生活秀》、《小姐你早》、《致无尽岁月》、《有了快感你就喊》等作品,池莉的小说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烦恼人生》中对印家厚充满同情,笔触侧重在生活对小人物的挤压,到了《来来往往》和《生活秀》中,池莉的叙事姿态更加从容。她不仅将叙事的重点放在日常琐碎生活的挤压上,更看到了在这种挤压下普通人生存的尊严和意义,尽管这种意义中甚至包括一种反传统道德的世俗欲望和混沌的生存状态。在这些作品中,花心老板康伟业,卖鸭脖的女老板来双扬,包括苦苦挣扎的卞容大,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他们的爱恨情仇,屈辱和反抗,都有了一种无可辩驳的合理性。她的近作《托尔斯泰的围巾》,更是一部有代表性的小说。小说中出现了一个“老扁担”的形象,叙事机智,生活气息浓厚,小人物的生存尊严问题,不仅从世俗化的欲望上,而且从小人物的精神追求层次上展现出来,表现了池莉近年来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新探索。与池莉对市民主义的理解姿态不同,方方近期的创作,则更富有批判性和反思性,如《树树皆秋色》、《水随天去》、《奔跑的火光》、《出门寻死》等系列中篇小说,既延续了新写实小说冷峻的现实主义风格,又避免了“零度叙事”、细节生硬琐碎的缺陷,发挥了女性特有的敏锐、悲悯和细腻,在深刻反映现实生活悲剧的同时,注重以感性的情感剖析生活,风格柔中带刚,追问社会转型期弱者的伦理和生存的困境,显示出越来越成熟的创作状态。《奔跑的火光》中对农村女性的关注,《水随天去》中少年水下在青春欲望和伦理之中的挣扎,都在娴熟的叙事中彰显出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刘醒龙的《凤凰琴》、《秋风醉了》、《分享艰难》等作品,一直紧密关注现实生活的矛盾冲突,从民办教师的令人触目惊心的困难和对祖国的赤诚,到基层官员在盘根错节的现实问题前的迷茫,国有企业转型的艰难和困境,都展示得异常真实而严峻。在这些作品中,刘醒龙不回避困难,不遮蔽矛盾,而是致力于揭示社会转型期的复杂性。例如,在小说《凤凰琴》中,在那不屈不挠地飘扬的红旗下面,没有太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没有完美无瑕的人格,却有着太多血与泪的困窘、无奈和悲伤。小说以一种触目惊心的形式,还原了生活的残酷,也真实再现了人性的挣扎与绝望。
其次,艺术的多元性和探索性,也是湖北中篇小说创作的一大特点。湖北作家不仅有着批判现实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也有着楚风熏陶下的对艺术的浪漫灿烂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的目光不仅放在农村生活的艰难和都市世俗人生的悲喜之中,而且深入人与自然的关系,探索小说写作形式在楚风传统和现代性之间融合的可能性,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生态小说、邓一光的浪漫主义小说、晓苏的“油菜坡”系列小说,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松鸦为什么鸣叫》、《狂犬事件》、《太平狗》、《失语的村庄》等小说,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他的“神农架系列小说”有力地参与“底层叙述”,继承中国文学的“悯农”传统,将人文精神融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阶层差距对人性的伤害等等沉重的话题,他关怀底层贫民,展示出一个在大自然的神话与现实之间交错,又充满了忧患和愤怒、失望与希望的奇特的艺术世界。他的小说不仅具有丰富的生活气息和现实质感,而且有着神秘性、想象性的楚风特色。他擅长于在限制性的视角叙事之中,通过富于象征性、寓言性和神秘性的意象,荒诞的人物形象,传奇的故事细节,构建多层文本对话意义上的小说美学。《马嘶岭血案》一直借用杀人者“我”的视角来叙述整个故事的始末。最终也用“我”那一句“这是为什么呢?这种想法让我至死也弄不明白”结束了整个故事。比较而言,邓一光的小说以其英雄气质和诗意的叙事,为人称道。他的《狼行成双》、《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想起草原》都艺术地展示了在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内,英雄主义和诗意在残酷冷漠的现实面前的失落和悲剧感。特别是《狼行成双》,作家将狼对自由和爱情的追求,化作了一曲浪漫主义的绝唱,读来让人潸然泪下。近期作品《我是太阳》,则将两位战争老人置于巨大的历史漩涡之中,用浓烈的激情,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再现了历史沧桑中英雄主义的浪漫坚守。而晓苏则以《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等小说对校园知识分子戏谑式的解构确立了自己的艺术个性与艺术风格。
再次,湖北的中篇小说创作还具有着特殊的先锋气质和青春气息,这主要体现在一批极有潜力的青年作家的创作中。刘继明、张执浩、晓苏、李修文、姚鄂梅、胡发云等青年作家都以其崭新的美学原则使湖北的中篇小说呈现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刘继明以一个流浪歌者的诗性吟唱从“60年代”作家群中脱颖而出,日益成为新世纪文坛上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前往黄村》、《海底村庄》、《明天大雪》、《桃花源》、《中国迷宫》、《我爱麦娘》等系列“文化关怀”小说在文坛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前往黄村》在解构了黄毛的英雄主义喻指的同时,也无情地讽刺了世道人心的堕落。《海底村庄》则利用封闭的寓言模式,虚构了欲望蓬勃的无耻的力量和精神追求的残酷对比。青年作家李修文也有着独特的文学气质,他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叫《心都碎了》,非常好地显示了李修文小说创作本质特征――他是那样深入地体验着人物的内心,往往能把人物内心深处那矛盾着、撕裂着、悸动着的灵魂写出来。他常常是和笔下的主人公一起经受着灵魂的锻打和锤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