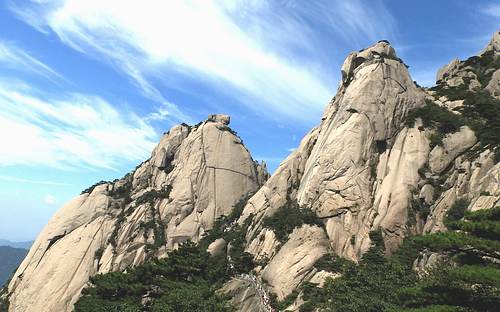其亡也忽焉
泱泱大国,就这样轻而易举毁于竖子宵小只手!痛心、悲愤、无奈、惋惜、惆怅的情绪,伴随着阅读这部书的全过程。何等富强的一个大国!何等豪迈的一个民族!何等辉煌的历史时刻!转瞬间,灰飞烟灭。残暴的项羽,狡诈的刘邦,阴狠的赵高,优柔的李斯,迂腐的扶苏,守正的蒙恬,傻浪的胡亥,蒙昧的陈胜……这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这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时代,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少有的大出血大疼痛的时代。
这次不想从大的角度来解读,且选择李斯这个小切口。因为这场史无前例的华夏乱局,是从李斯的动摇开始的。
李斯本是正道之人。正道之人,当行正道,走邪道本不是擅长的事情。李斯有思想、有才能、有眼色、有担当,故能在始皇时期立下赫赫功劳。然而,在始皇薨去这一重大历史节点上,他的私欲爬出来了,更多从自己的角度而不是帝国的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说白了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重。扶苏与胡亥,是个人就知道谁更能担得起繁荣帝国的大任,只有他李斯揣着明白装糊涂,欺骗别人特别是欺骗自己,不断地在道义上说服自己,给自己的愚蠢行为戴上合理化的帽子。当他把自己考虑得比帝国大计更重要的时候,已经偏离正道了。他磕磕绊绊在邪道上蹒跚、彷徨、犹疑的样子,多么可笑,又多么可悲。不管他怎么欺骗自己说胡亥和赵高多么无能他也能力挽狂澜,帝国和他自己的悲惨命运在他作出错误选择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
李斯有本事,是干才,是能人,从事业角度来看,掌握大权是没问题的,他自己也是如此认识自己的。然而,执掌中枢之人,除了才能,更重要的要有一种盛德。大秦历史上,秦孝公、惠文王、昭襄王都无大才而能兴国,都是盛德之故。何谓盛德?盛德是运筹全局的大算,是进取腾挪的机变,是容人纳谏的雅量,是大公无私的胸怀,是果敢能断的决心,是百折不挠的韧劲,是知错能改的虚心。没有这些,是无法让跟随自己的人安心、热心、忠心的,而这正是李斯所欠缺的。历史地看,同是秦国丞相,李斯比商鞅、张仪自是不及,和吕不韦比更是差了一大截,偏偏他又想成就堪比商鞅的大业,偏偏他掌握着帝国最大的权力。不禁要感慨:世界上最悲哀的事情,也许就是孜孜不倦地去追求自己能力之外的事业,俗称作死;更悲哀的是,拉着更多无辜的人跟着你去送死。
政治的根本在于人,你可以不钻营人事,但绝对不能不通人事,特别是奸臣当道、政治黑暗的时候,更要有这种意识。因为政治清明的时候,自有皇帝主持公道,而当政治黑暗的时候,你若没有力量,只能任人宰割,因为奸臣从来都是不讲公道的。李斯的可悲之处,就在于他在政治上从来都是孤立的,虽然整个帝国的所有大事都是他在运筹,但他身边始终没有聚集起一股可以反抗奸邪的力量,反而是支持信任他的人越来越少,甚至本来在同一阵营的人都对他心灰意冷。人事方面,他甚至连秦王子婴都不如。为何子婴能收拾赵高而李斯不能?就在于子婴明白,跟流氓不能讲道理,而要纠集力量收拾他!打怕了,他就服了。只用一个内应、两个王子,子婴就干净利落收拾掉了赵高;而李斯手握大权的则是进退维谷、左支右绌,只能眼睁睁去送死。不亦悲乎!
在《一级恐惧》的影评中谈到过这个问题,就是善良的人总倾向于以己度人,以为邪恶之人在内心深处是和自己一样的,至少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一样的,对善恶的理解的是一样。正是这种思维,使得善良的人在面对邪恶之人的时候往往被骗。事实是,邪恶之人思考问题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两者的区别比大象和蚂蚁的区别还大。善良的人应对邪恶的人,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范蠡、张仪等人的路线,躲得远远的;另一条就是《九品芝麻官》的路线,不以己度人而是以人度人,变得比奸人更奸诈。第二条李斯肯定是做不到的,那就至少躲远一点啊,咱不走邪道走正道不行吗?蒙恬、扶苏固然政见不合,但至少他们不是小人、也不会这般狠毒,他们上台最多失势肯定不至于丢命,更不要说给帝国带来如此沉重的灾难了!就是因为一时拎不清,守着一点小私心,看不长远,只想保住眼前的利益,结果哗啦啦失掉了全世界。这一切都是他自找的。想对所有善良的人说一句,宁与君子较量,不与老虎谋皮,后人万不可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秦亡论(大秦帝国)书评
当国家快速发展时,速度掩盖了问题;当国家发展停滞时,问题被无限放大。
最可怕的敌人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内部的腐化堕落。
为何赵高之流能逼死百官,作威作福?因为他控制了胡亥,挟皇帝以令百官。在秦朝,“成法立制,终决于人”,以皇帝为轴心的庙堂,是天下法律的源头。赵高借助皇帝的权利,把法律当做工具般如臂指使。俗话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像赵高这般精通大秦法律,少之又少了。
三公九卿制度实际上丞相一家独大,在没有秦始皇般目光如炬地盯着李斯,李斯的野心和权力空前地膨胀起来。当他宣布立胡亥为二世皇帝时,满朝大臣竟敢怒不敢言,无人去制约李斯的空前权力。
英明神武如始皇者,却在立太子上面,踌躇不决了几十年,乃至在临死时,也没有明说立谁为太子,写下残诏,给赵高、李斯之流可趁之机。
假如早早立扶苏为太子,秦朝二世而亡未必尽然。
秦始皇酷爱读《韩非子》,却没有将法、术、势的思想,实际运用到帝国管理上。赵高,伴随始皇一起长大,大大小小处理过不知多少的私事,是始皇的忠实奴仆,然而小高子,私藏遗诏,以求权力晋升,可见狼子野心。李斯,大秦王朝的缔造者之一,为秦国统一六国殚精竭虑。但在政治上立场向来不够坚定,与始皇政策常年一致。大将王贲临死前曾说,“李斯斡旋之心太重,一己之心太过”。另外李斯出行,仪式繁华,可见有私欲,只不过因为始皇在而稍加克制。
扶苏面对李斯和赵高编纂的假诏,竟然信以为真,应诏赴死,当真迂腐之极。而蒙恬却半信半疑,没有立即和扶苏率军南下,拥兵继位。
满朝文武大臣,一忍再忍,对皇帝和李斯抱有幻想,当真可笑。假如有王煎、王贲父子任何一人在,当拥兵入咸阳,用锋利的剑刃插进敌人的胸膛,杀伐果断之极。
秦朝初立,镇守各方的多是秦氏部族,导致关中尽是他乡之人。秦氏部族的凝聚力被削弱了。导致后期章邯只能用刑徒军对抗反秦势力。
假如关中还有还有数万大秦铁骑,随便一个秦军将领都可以横扫这些乌合之众。
1.六国复辟势力此起彼伏,复国野心从未消退。
张良、项羽在秦朝末期,左右逢源,都能拉出队伍和秦军对抗。
2.土地兼并、沉重的徭役失去了民心。
众所周知,一个王朝失去了民心,那它走向了末路就不远了。古往今来,皆是如此。
当时的秦国可真是糟透了,里有胡亥、赵高之流祸国乱政;外有农民起义、军阀割据;北面还有日渐强大、蠢蠢欲动的匈奴部族,当真回天乏力啊!
终其根本,亡秦国者,非六国也,乃秦国也。
看到亲手创造的秦朝大政被破坏的支离破碎,始皇大帝也会泪目吧!!!
《大秦帝国》赞
我大秦从不残暴,今人不能用现在的文明标准来苛求古人,再说还是战时法制! “有功于前 不为损刑 有善于后 不为亏法”正体现了法制的严肃性;“刑上大夫 礼下庶人”体现了法制的公平性;“国无二法”体现了法律的权威性;”大仁不仁”体现了法制的前瞻性,目的不是以施暴为目的而是以防范犯罪为最终目的以震慑犯罪为目的。~试想想如此公平合理的司法实践就是到了比2000多年前文明的今天能做到吗?“ 秦灭六国是统一的需要,见过大规模屠杀六国人民的屠城行为吗?见过屠杀六国贵族吗?从而给自己埋下复辟的祸根!见过“狡兔死 走狗烹 敌国灭 谋臣亡”的统一后大肆屠戮功臣吗? 至于修复道路发明驰道,决通川防,建立路政系统,都江堰与郑国渠还有灵渠等水利工程,还有连接长城,哪一项不是造福子孙造福华夏的大事?大力征发民力和50年代的大跃进何其相似?求治过急不能用残暴二字形容!我替秦人叫屈!我先祖如此辛劳的为天下计为子孙后代计怎么就暴秦了? 至于坑儒一说也是依法杀人并非滥杀无辜,法律在前一般刻意复辟的儒生和六国复辟势力勾结一气想颠覆国家不为国家建设出力而造谣生事的不该杀吗? 至于阿房宫焉知不是建造新都?咸阳已经对一统后的江山而言太小了!至于始皇陵那是法制扭曲以后变味的产物。 蒙恬30万秦军若不是肩负华夏重任防范匈奴南下(后期汉高祖被困就是匈奴强大的铁证)岂有项羽之辈丝毫机会? 若非50万秦军南下为后世开辟广大的疆土,现在的福建两广贵州云南恐怕就是外国了! 若非华夏族群意识50万南海军北上哪有刘邦项羽?带甲百万的赵佗后来归附汉也决非实力不济(有兴趣的可以查赵佗上汉景帝书,其中一句引人泪下:不敢忘先人之志也!) 呜呼哀哉!为华夏族群留下丰厚家产的秦人部族历史上却留下暴秦骂名,能不痛心疾首吗?
上篇:小时候的感悟